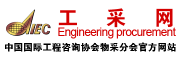中国资本走出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符合邓宁“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描述的阶段特征。相比“引进来”,中国资本“走出去”起步更晚,但步伐更快。两者有显著的结构差异,且存在时变特征。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存量就已经超过外商直接投资(FDI)。但是,中国ODI仍面临政治和法律等风险的挑战,民营企业同样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短板不是硬实力,而是软实力,服务业发展水平至关重要。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及中国实践
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需要两个条件:推动力和吸引力。前者针对母国,后者针对东道国。推动力又可分为宏观、产业与企业三个层面。宏观方面,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和“折衷理论”(Dunning,1981;迪肯,2009),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第一阶段(人均GNP低于400美元,1971年美元计算),母国三大优势均欠缺,FDI与ODI规模均较小;第二阶段(400-1500美元),区位优势增强,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仍然欠缺,FDI规模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仍然较小,直接投资顺差规模不断扩大;第三阶段(1500-4000美元),三大优势同步增强,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加,直接投资顺差逐渐收敛至均衡;第四阶段(4000美元以上),三大优势进一步增强,ODI规模超过FDI,直接投资转变为逆差。四阶段的划分来源于经验数据,不同国家会有不同,但对外投资与人均GDP正相关已是学界共识(李辉,2007;薛求知,2007)。
中国直接投资状况基本符合理论描述(图1)。按现价美元计算,中国人均GNP突破400美元、1500美元、4000美元的时间点分别为1993年、2004年和2010年。第一阶段,1993年以前,FDI与ODI规模都比较小(但FDI始终高于ODI);第二阶段,1993-2004年,FDI大幅流入,ODI仍然低位运行,直接投资顺差于1993年跳升至231亿美元,2004年达到550亿;第三阶段,2005-2010年,FDI规模持续增加,ODI在2005年首次突破百亿后以更快速度增加,直接投资顺差在2005年达到600亿美元后开始下降。第四阶段,FDI增速放缓,2015-2019年连续逆差(不同统计主体或货币单位会有差异)。2019年,中国人均GNP已经突破1万美元,所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宏观层面的推动力已经具备。2016年以来,中国ODI开始持续收缩,宏观层面主要是由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和中美贸易纠纷等原因导致的。除了经济发展阶段,文化、法律等制度以及服务业发展水平都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
图1:中国直接投资的阶段性特征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UNCTAD,WIND;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注释:由于是以现价人均GNP划分阶段,故曲线会向右拉伸。
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因素着眼于企业管理和战略。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主要包括:获取资源、寻找市场、提高效率和战略资产。国内劳动成本的提升是企业外迁的重要原因。2005年前后,中国劳动市场的刘易斯拐点出现(蔡昉,2014),农村转移的劳动力开始从过剩转变为短缺,非技能劳动力工资开始上升。2011年前后,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工资上涨压力进一步增强。劳动密集型企业从沿海地区内迁移至中西部,或外迁至东南亚等国,以缓解成本压力。中国制造的另一项重要约束条件是自然资源,所以能源或金属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例较高。例如,2005至2019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近1,000亿美元,其中700亿投资了能源和金属。
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主要是指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良好的制度(政治、法律和市场等)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均是吸引外资的优势条件。当然,母国与东道国的“制度距离”也会影响直接投资,政治和经济制度相近的国家更易达成交易。无论是制度质量,还是制度距离,显然不能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和近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是因为,实证研究发现,双边投资协定能够弥补东道国的制度缺陷,或缩小制度距离(宗芳宇等,2012)。综合而言,企业只有在满足“折衷理论”的三个条件时才会对外投资,进行跨国生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事实
2000年,党的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走出去”战略,并于2001年被写入“十五”计划。2005年,ODI规模突破百亿美元,此后加速扩张。2012年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加速实施“走出去”战略,2013年提出了“一带一路”(BRI)倡议。2015-2018年,ODI流量持续高于FDI,直接投资连续四年出现逆差(如果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仅2016年为逆差。)。
从2013年开始,中国ODI年流量就超过了千亿美元,2016年达到两千亿,为历史峰值。截止到2019年底,中国ODI存量约2.2万亿美元,高于FDI的1.8万亿;境外企业总资产达到4.4万亿美元,相比2008年增加3.4万亿;境外企业就业总人数在2018年达到峰值,为359.5万人,2019年降至274万。其中,外方就业人数在2014年之后快速增加,2018年为187万,占比52%,2019年增加至227万,占比达83%。分企业的性质来看,国有企业占比持续下行,至2019年底仅为5%(2007年占比约20%),私营企业在2016年跳升至26.2%,相比2015年增加17个百分点。分投资形式看,跨境并购(M&A)为处于绝对主导地位。
图2:中国ODI地域分布
数据来源:商务部,WIND,东方证券
从行业分布看(图3),租赁和商业服务排在首位(占比约1/3),其次是批发和零售(占比11%)。2016年开始,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占比明显提升,2017-2019年占比平均10%。制造业和采矿业占比分别为9%和8%。当然,在不同地区或国家,行业分布有较大差异。
图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
数据来源:商务部,WIND,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亚洲。流量方面,2016年以前持续上升,2016年峰值为1,300亿美元,2019年收缩至1,100亿。2007年以来,亚洲占比基本在60%-80%之间。2016-2019年,占比连续提升,2019年达到了81%,为历史峰值。存量方面,截止到2019年底,亚洲ODI存量为1.46万亿,占比66.4%。香港作为中国资金的“出海港”,占亚洲ODI存量的约90%;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仅次于香港。从行业角度看,香港ODI规模最大的是租赁和商业服务,其次为金融业和批发零售;其余亚洲国家,规模排名前四行业为能源、运输、金属和房地产。
美洲。2006年之前,拉丁美洲是除亚洲之外中国ODI最主要的目的地,2005和2006年占比分别达到了45%和48%。2006底,拉丁美洲占到了中国ODI存量的26.3%。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ODI更偏向于亚洲、北美和欧洲,拉丁美洲占ODI存量的比重至2019年底降至20%,仍位列第二,总金额为4,300亿美元,其中,开曼群岛为2,800亿,占比65%,英属维京群岛1,400亿,占比33%,两大避税岛合计占比88%。北美方面,2016年以前,中国对北美洲的直接投资持续上升,2016年达到200亿美元峰值,其中,170亿流入美国。2017年以来,规模锐减,当年仅为65亿(基本都投向了美国),2018年小幅反弹后(87亿),2019年进一步收缩至44亿美元(美国38亿),仅占当年ODI流量的3%。截止到2019年底,中国在北美的ODI存量仅为1,000亿美元,仅为拉丁美洲的23%,全球占比4.6%。如果不考虑避税港,美国是中国在美洲最重要的直接投资目的地,其次为巴西和加拿大。对美国的投资主要分布在房地产、金融、运输和技术,巴西和加拿大主要是能源,秘鲁是金属。能源、金属和房地产是中国在北美投资的前三大行业。
欧洲(含俄罗斯)。中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起步较晚,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才显著加速。2008年以前,ODI流量基本位于30亿以下,所以,截止到2009年底,存量仅为86亿美元。ODI流量的峰值出现在2017年,为184亿美元。至2019年,ODI存量达1150亿美元。分不同国家来看,由于荷兰是流入欧洲资金的中转站,ODI存量达240亿,占比21%,紧随其后的是英国和德国,分别为170亿和142亿。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统计,以项目最终目的地和投资额计算,英国、瑞士和德国排名前三,法国和意大利位居第四、第五。各国的行业分布主要是:英国的金融、房地产和物流;德国的交通运输;瑞士的农业;法国的能源和旅游;意大利的交通和能源。整体而言,截至2019年底,制造业、采矿业和金融业是中国在欧盟投资的主要行业,ODI存量分别为310亿、165亿和150亿美元,合计525亿,占比46%。
非洲。2003-2019年,非洲ODI流量仅在2008年和2018年略超过50亿美元,大多数年份位于30亿美元以下。截止到2019年,中国在非洲的ODI存量约450亿美元,南非和刚果金是仅有的两个超过50亿美元存量的国家。从行业分布上来看,能源和金属项目占绝对主体地位,总金额占比约80%(美国企业研究所数据)。
“一带一路”。自2013年启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以来,中国在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快速增加,2014-2019年均超过1,000亿美元,截止到2020年底,项目金额总计达到7,600亿美元。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2020年上半年仍然达到465亿。新加坡、意大利、秘鲁和印度尼西亚是重要目的地。能源、金属和交通运输是重点行业(图4)。从ODI存量上看,占比约13%。近年来,一带一路投资引发的债务问题和项目的可持续性引发广发关注。据AEI统计,2005-2020年(H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共出现300个陷入困境的交易项目(Troubled Transactions),总金额近4,000亿美元。其中,一带一路项目占到了160个,涉及金额1,600亿美元。
图4: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
数据来源:AEI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中国对外投资过度了吗?从横向对比来看,发展中国家ODI占GDP的比重平均为23%,超过中国8个百分点(图5)。全球平均水平为40%,发达国家为53%。在全球主要的35个经济体中,中国大致处于25%分位数的水平。所以,并不存在过度的问题。过度与否的判断标准并不是投资的绝对或相对数量,也不是与其他国家比较所处的位置,而在于投资项目是否符合经济意义上的投入产出核算,或者是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战略。如果中国想要持续对外输出资本,在没有取得一定的金融话语权的情况下,纯粹出于政治考虑,经济意义上的可持续性就会大打折扣。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快和居民储蓄率的持续下行,中国经常账户将维持在基本均衡的状态,时而逆差将是常态,尤其是在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的转轨过程中。中国的ODI,不再是经常账户顺差,而是FDI,抑或对外投资项目的再投资收益。可以想象一条ODI的“可能性边界”,它主要由经济因素决定,但国内外政治因素对项目成功与否至关重要。
图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比)所在分位
数据来源:UNCTAD,WIND,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全球化智库(CCG)分析了2005-2014年间120个投资失败的案例,发现25%的是由于政治原因(其中的8%是因为东道国政治党派的阻挠,另外17%是政治动荡或政党更替),另外还有16%与法律风险有关(其中三分之一是由于不了解或不遵守法律,另外三分之一是由于不熟悉劳工法规)。不同国家针对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反垄断法规、环境保护法规、劳工法规和税收法规等均不相同,并且还根据政治经济因素不断变化,这导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面临重大法律风险。大多数中国公司缺乏国际经验,也不熟悉外国的法律。这使得这些公司与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的法律风险特别高。
综合而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对的挑战包括:规划与战略、风险管理、融资渠道、缺乏合作、企业国际化水平低、中介服务利用不足、不善于应对东道国复杂环境的挑战、跨文化差异(Hui Yao Wang and Lu Miao,2019)。中国对外投资的短板主要不是科技的硬实力,而是服务的软实力。无论是对国内居民的美好生活,还是对于中国资本走出去,服务业发展水平都是关键,这又与服务业的开放水平直接相关。
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执行主管